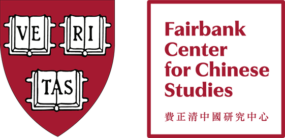楊富閔,出生於台灣解嚴的 1987年,是台灣新一代寫作者中的佼佼者,而他同時也是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,並於 2017年1月至8月期間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。楊富閔目前出版有小說集《花甲男孩》(2010),散文集《解嚴後台灣囝仔心靈小史》(2013)與《休書:我的臺南戶外寫作生活》(2014),田野踏查誌《書店本事:在你心中的那間書店》(2016),並且纂輯《那朵迷路的雲:李渝文集》(2016,與梅家玲、鍾秩維合編)。二O一七年作品《花甲男孩》由台灣「植劇場」改編為電視劇。
文字整理:鍾秩維,台大政治系、台文所碩士班畢業,現為台大台文所博士候選人。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Hou Family Fellow (2016–2017)。

鍾秩維(以下簡稱鍾):《花甲男孩》是你的第一本書,出版距今已經七年!可否請你先談談其成書的經過,並且聊聊你近幾年來的寫作?
楊富閔(以下簡稱楊):《花甲男孩》是我在大學時期完成的一本短篇小說集,總共收錄九篇作品。它起於〈暝哪會這呢長〉而結束在〈花甲〉──花甲是個大學生,姓花名甲,我很喜歡這個名字。而雖然集中都是短篇小說,結集後我自己再看過一遍,覺得它其實具有一個長篇的格局,留下了許多未竟的線頭。
完成《花甲男孩》以後,我到台大讀書,同時身兼研究與創作者的身分,記得許多人問我,兩者會不會有衝突?如今回想,研究與創作不但不相牴觸,反而能夠彼此增補。因為學術研究的緣故,我對於文學的既定認識不斷被鬆動,大量閱讀史料和文本帶領我到許多未知的地方,而在這一過程中,文學與歷史的交織,給了我特別多的刺激。後來我的寫作相對專注在自傳性的素材,可能原因出在於此。我很想要將「我」的存在釐清。對於自身的所來與所去,一直是我寫作的興趣所在,而研究所的訓練,剛好補強了我的歷史課題。
《花甲男孩》之後寫的幾本書,文類上接近所謂的「散文」,甚至有點踏查誌的味道。然而去年在改編《花甲男孩》為電視劇的討論會裡,看到來自文學、戲劇與影像等不同領域的從業者,分別從其專業一起來述說《花甲男孩》故事的時候,我突然意識到,這些年來我的寫作其實是在「說故事」。亦即不論寫的是小說或散文,我覺得我都是在尋找一種說故事的方式,同時也在觀察故事在當代社會、媒介其出現與傳播的型態。也許我的寫作是透過自身的生命經驗──說「我」的故事──去回應當代的時空情境;換言之,去想像與開發一種足以顯示當代性的文體,是我努力的目標。

鍾:你的作品常常穿插其他的文學文本或史料,也有很多關於不同媒介經驗的描述,可否請你聊聊你的文學啟蒙,以及你是如何「讀」文本的?
楊:每當被問到文學的啟蒙、養成與訓練時,我都非常慌張!我出生於1987年,適逢台灣解嚴,生長在台南一個鄰近曾文溪的山區聚落──大內──的一個超級大家族。我的家族有自己的宗祠、田地,而家族的長輩在宮廟活動中總是擔綱重要角色,故而,我從小最多接觸的就是祭祀,以及廟宇相關的活動。
記得童年時我和哥哥常一起在客廳塗鴉,畫的內容即為廟會遶境,「遶境」的逡巡方式,每每讓我想起自己是住在一座海島。而也許因為生長在一龐大的家族,我的「轉大人」同時是伴隨無數長輩的亡逝。我喜歡廟會也喜歡葬禮,有一種喪葬的陣頭叫做「牽亡歌仔」,表演者會和家屬互動,一方面有勸善教化的作用,同時也具備撫平悲傷的功能。我是「牽亡歌仔」的忠實觀眾,不但不覺得禁忌,還常跑到喪家去看這種既說且唱的陣頭。到現在我仍常在youtube搜尋神明出巡抑或喪禮儀式的影片,一邊看一邊做筆記。民間藝陣非常吸引我。
我從小也是個電視兒童。那是第四台開始的年代,電視頻道一百多台。那時我的房間就有台小電視,看電視的時候,也就是我獨處的時候。而我其實不大看卡通,反倒是當時許多地理探索、行腳台灣的節目比較吸引我,比如《台灣探險隊》和《台灣全紀錄》。
而在國中一年級的時候,家裡有了第一台電腦,想來這也是個關鍵時刻。現在回過去看,覺得無論是庶民生活的民俗活動,或者電視電腦不同媒介的閱聽經驗,都是我接觸與想像「文學」的方式,是我的文學啟蒙。
電腦來的那年,大概是二OOO年,新舊世紀之交,於我而言更是生命的重要轉折──先是九二一大地震,接著台灣首次政黨輪替;我升上國中一年級,離開生我養我的故鄉大內;我家的曾祖母也在這年過世,她活了一百O二歲。
鍾:聽起來你的寫作非常「接地氣」,能否請你分享更多文學與生活相連結的故事?
楊:去年(2016)我哥哥結婚,我父親託我替他擬一份稿子,說是祭祖的時候要念給祖先聽;與此同時電視劇《花甲男孩》也在改編,其中有篇祭文,導演也請我試著寫寫看──我寫過小說故事、記人寫物的文章,訪談與論文,但從沒寫過祭文!但我很願意去嘗試,而且樂在其中。我覺得作為寫作者什麼都要去寫寫看,更重要的是,去留意「文字」是如何被妥貼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。這幾年也在寫作專欄,專欄經營須顧及字數限制(1000或5000字),而且講究時間規劃(每周一篇或隔周一篇),遂使我的寫作更為規律,而且有了某種紀律要求。這樣的規律和紀律促使我更學習掌握「寫作」所需的時間,包括事前的閱讀與事後的養息,而對於寫作過程中的生、心理變化亦有更多的注視,就像是用寫作在健身!
而各種文體中我寫最多的其實是日記,包括無時無刻都在做的筆記。但寫最多的日記,反倒是我認為最難寫的文體。在當代,比如一台手機,它能夠為個人留下難以估量的數據資料──去過的地方不僅可以被追蹤,甚至連里程數都有紀錄;行事曆清楚記載大小工作規劃;網頁瀏覽紀錄反映了使用者興趣之所在……關於「我」的一切被各種數據紀錄、呈現。在這種錙銖都被網羅的情況下,什麼才是一天之中「我」真正想要記得、留下來的?寫日記──定時定點整理與反思──在這個意義上就像是健身,用文字鍛鍊自己的心性,探索心靈的邊界。
鍾:剛剛你談到了小說《花甲男孩》改編為電視劇《花甲男孩轉大人》的過程給你的啟發,能否請你就這個部分再多談一點?
楊:文學的影視改編是一種多方跨界的合作共振,從中我們可以觀察一則故事在不同媒介之間的流轉衍生,而它同時也牽涉到不同的專業領域,比如服裝造型、燈光與美術,如何就共同的題目各自創作、各自用他們的方式說這個故事。
而這次收看電視劇的時候,我也開始思考傳播媒介的多樣性,它是如何影響我們對於一則故事的理解──故事的另一種版本是不是隨時在發生?像是螢幕的不同規格(尺寸大小、畫素高低)可能就會影響到觀眾對於故事的接受──我用手機看、耳機聽,連風聲都聽見了,演員的膚質也一清二楚──而讓觀眾能夠看得更精更細的這些那些高科技,連帶也促使我去觀察當代的演員的表演方式,拍攝製作須服膺何種新的專業要求,而劇本、乃至於文學的寫作,又轉化出什麼不同的可能,等等的問題。
對於習慣文字思考的我,這些都是相當寶貴的經驗──影像展演如何回應文字表述,文字如何具備影音的質素,文字有沒有高清的問題?這個世界越來越清楚了嗎?以上提問都還有待我去探索。
我從小喜歡寫作,寫作就是我的初衷。而我對於探索自身的所來與所去,總是懷有一股難以述說的狂熱。我熱愛這塊土地,更熱愛述說故事,我常覺得,可以說故事給大家聽,是我最大的榮幸。
楊富閔是台灣新一代寫作者、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。
鍾秩維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 Hou Family Fellow (2016–2017)。